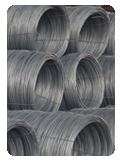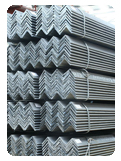柞水的四季是把算盤,打得清爽分明。春是山桃野杏漫出來的粉,夏是秦嶺深處浸在溪水里的綠,冬是雪落秦嶺時壓著松枝的白,到了秋,便成了一場雨一封信,拆開時總帶著點涼津津的新意。
最先察覺秋來的,該是山尖的風。先前夏末的風還帶著溪澗的潮氣,黏在皮膚上是溫吞的,忽然某夜落了場雨,不是夏日常見的瓢潑,是細密的,像誰把云撕成了絮,飄著飄著就沉下來。雨絲落在柳樹的葉上,起初是綠得發亮,積得多了,葉尖便垂下來,像噙著淚的眼。晨起推窗,原先是開滿花園的各色花,經了這雨,花瓣就蜷了邊,連帶著墻角的狗尾巴草,也少了幾分張揚。
再下幾場雨,山就換了衣裳。楓葉先是淺紅,被雨一淋,便濃得像化不開的胭脂,沿著山脊鋪過去,竟比春時的花海還要熱鬧。板栗樹的葉子黃了,風一吹,便簌簌地落,鋪在山路上,踩上去軟綿綿的,帶著股清甜味。山民們開始忙了,背著竹簍上山摘板栗,收核桃,額頭沁出的汗,被風一吹,竟有些涼——先前穿單衣還嫌熱,如今薄棉襖也得備上了。
溪澗的水也瘦了,先前嘩啦啦地奔,如今卻緩了許多,清得能看見水底的鵝卵石,映著兩岸的紅黃綠,倒像幅流動的畫。傍晚時,炊煙在村子里繞,混著飯菜香飄出來,行人不由自主地緊了緊衣襟,方才察覺風中桂花的香氣已悄然淡去,菊花開得正盛——這場雨過后,怕就是霜降了。
柞水的秋,原是藏在雨里的。一場雨,剝去一層熱,露出一層涼,把山山水水都洗得分明,也把日子過得扎實。等最后一場雨落盡,雪就該來了,可那又何妨?畢竟這秋,已被記在心里了。(大西溝礦業: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