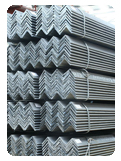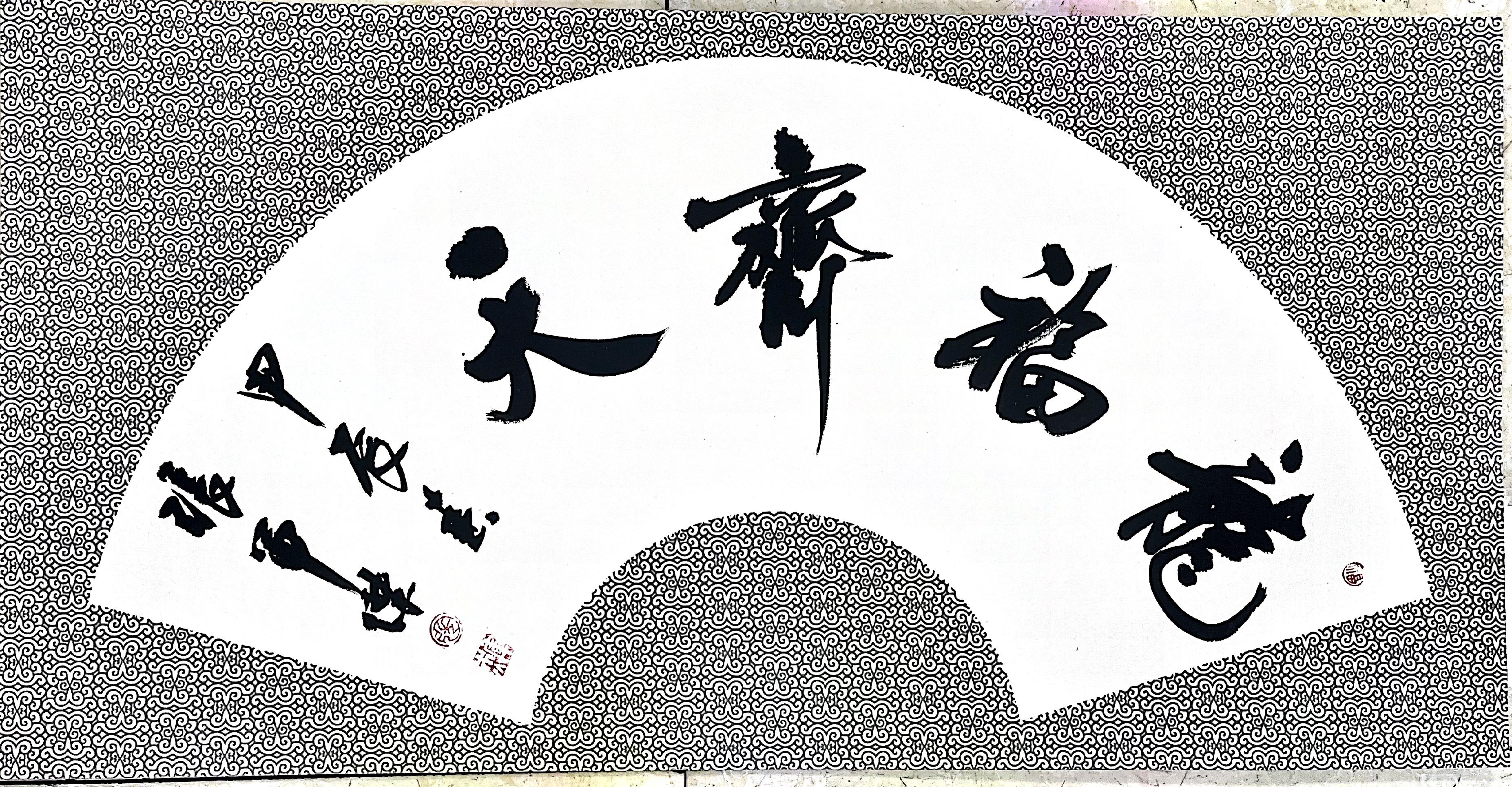母親是閑不住的。
這并非說(shuō)她天性勤勉,而是她的雙手仿佛自有意志,容不得片刻清閑。我幼時(shí)的記憶里,母親的身影總是鑲嵌在各種活計(jì)中,如同一幅永不靜止的動(dòng)態(tài)畫(huà)。
天還未亮透,母親便已起身。先是廚房里鍋碗輕碰的聲響,如晨曲的前奏;繼而是灑掃庭除,掃帚劃過(guò)地面的聲音規(guī)律而綿長(zhǎng)。待我們?nèi)嘀殊焖燮鸫矔r(shí),熱粥小菜已妥帖地?cái)[在桌上,屋里屋外纖塵不染,而母親額上已沁出細(xì)密的汗珠。
母親的“閑不住”滲透在每一個(gè)日常縫隙里。吃飯時(shí),她總最后一個(gè)落座,第一個(gè)起身;看電視時(shí),手里必握著毛線針,上下翻飛間,毛衣便一寸寸生長(zhǎng);即便與人閑談,她也一邊剝著豆莢,一邊縫補(bǔ)衣物。我曾好奇問(wèn)她:“媽,您就不能真正閑一會(huì)兒?jiǎn)幔?rdquo;母親只是笑道:“閑著反而不自在。”
這種“不自在”我后來(lái)才懂得。母親生于上世紀(jì)五十年代,經(jīng)歷過(guò)物質(zhì)匱乏的歲月。在她的認(rèn)知里,時(shí)間虛度便是罪過(guò),雙手空閑便是浪費(fèi)。她常念叨:“人活一世,草活一秋,總得留下點(diǎn)什么。”于是她留下了一柜柜手工縫制的衣裳,一罐罐精心腌制的醬菜,一床床厚實(shí)柔軟的棉被——這些都是她與時(shí)間博弈的戰(zhàn)利品。
記得那年我赴外地求學(xué),母親為我趕織毛衣。臨行前夜,她房里的燈亮到很晚。次日送我上車時(shí),她塞給我一個(gè)包裹,里面是那件織完的毛衣,還有一雙新納的鞋墊。“外面買的哪有自家做的暖和?”她說(shuō)得輕松,我卻看見(jiàn)她眼底的血絲和手指上的創(chuàng)可貼。
婚后我接母親來(lái)小住,本想讓她享享清福,她卻在我家陽(yáng)臺(tái)開(kāi)辟了“農(nóng)場(chǎng)”,種滿蔥蒜香菜;又向我鄰居學(xué)了做面包,從此我家烤箱罕有歇息之時(shí)。妻子過(guò)意不去,勸她多休息,母親卻說(shuō):“能動(dòng)就是福氣。真等到動(dòng)不了的那天,想忙也沒(méi)得忙了。”
去年秋天,母親突然病倒。躺在病床上的她,雙手終于不得不閑下來(lái),卻總是在無(wú)意識(shí)地做著編織的動(dòng)作。我去看她,她第一句話竟是:“陽(yáng)臺(tái)上的花該澆水了。”我握著她的手——那雙布滿老繭、關(guān)節(jié)粗大的手,突然明白這雙手從未追求過(guò)功成名就,只是固執(zhí)地將對(duì)家人的愛(ài),編織進(jìn)每一針每一線,烹煮進(jìn)每一飯每一菜。
病愈后,醫(yī)生囑咐靜養(yǎng),母親表面應(yīng)承,轉(zhuǎn)身又開(kāi)始在康復(fù)間隙做康復(fù)手套送給病友。“做慣了,停不下來(lái)。”她有點(diǎn)不好意思地解釋。陽(yáng)光透過(guò)窗欞照在她花白的頭發(fā)上,那雙忙碌的手依然停不下來(lái),卻顯得如此安詳而充滿尊嚴(yán)。
如今我才懂得,母親的“閑不住”實(shí)則是一種生命的修行。她用一生的勞碌,詮釋著最樸素的智慧:生命的意義不在于靜止的完美,而在于動(dòng)態(tài)的付出;不在于擁有多少,而在于創(chuàng)造多少。她的忙碌不是不知享受,而是將享受融入了創(chuàng)造的過(guò)程本身。
窗外月色正好,想起此刻母親應(yīng)該還在燈下縫著什么。或許是一件給孫輩的小衣,或許是一個(gè)給我們兄弟二人的護(hù)膝。那些針腳細(xì)密的物件,如同母親用時(shí)光寫(xiě)就的情書(shū),無(wú)聲地訴說(shuō)著:愛(ài),就是永不停止的創(chuàng)造與給予。
母親的雙手依然閑不住,正如這個(gè)世界永遠(yuǎn)需要被溫暖,需要被塑造,需要被熱愛(ài)。而這份“閑不住”,或許正是母親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遺產(chǎn)——在不停歇的付出中,照見(jiàn)生命最本真的光芒。(漢鋼公司公輔中心 王江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