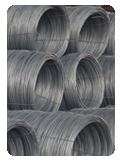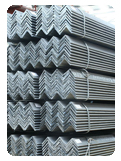陜北的秋意總是來得早了些。一場秋雨過后,夾雜著涼意的秋風染黃了山坡上的杏樹、山桃樹、白楊樹的葉子,山梁野口的黃蒿變成了浮萍,被吹卷著到處跑,嚇壞了在高粱地里覓食的野兔。不遠處的村莊,時不時傳來狗叫聲,打破了村子的寧靜,莊稼地里人們忙碌的身影,給蕭瑟的秋天增添了不少生機。
清晨的露水打濕了褲腿,透著秋帶來的涼意,那山頭的杏樹葉不等大地的召喚,早就發冠染成了暮年,高粱葉子在間隙中織起了“沙沙”作響的生命之網,似乎在訴說著獨屬于自己豐收的驕傲。趁著這清晨的涼爽勁兒,父親和母親在撿畔底下那片枯黃中帶了一絲綠意的玉米地里掰起了玉米棒子,母親在前面掰棒子,父親在后面砍秸稈,這些秸稈都是父親給羊儲存的過冬草料。早起的大公雞伸直了脖子打鳴,昂首挺胸地跟在父親身后,啄食著秸稈上緩慢蠕動的蟲子。當我說大公雞像父親的“護衛”時,父親笑著說:“咱家的大公雞可精著呢,一到收莊稼時就會跟在人的身后,啄食著秸稈上的蟲子,算是給自己加餐了。”
日上三竿,原本在晨光中若隱若現的遠處山巒,此時變得格外清晰,瓦藍的天上點綴著幾朵白云,瞬間把“秋高氣爽”展現得淋漓盡致。在陽光下,對面山坡上的金黃秋菊,這里一片,那里一片,給陜北的山花草木增添了不少活力。剛從煙囪里冒出的炊煙,立時被秋風吹散、飄遠,給秋日的畫卷增添了幾分生機。臥在窩里的大黃狗,也站起來抖了抖身子,找個暖和的地方趴下來,懶洋洋地曬太陽。父親放下手中的鐮刀,一屁股坐在玉米稈上,掏出旱煙鍋愜意地抽起了旱煙,灰白色的煙霧隨著他的呼吸緩緩飄散,順便帶走了他滿身的疲憊。父親對我說今年的玉米收成不錯,院子里那兩個巨大的籠架也不一定裝得下,說著說著,那嘴角的微笑把眼睛拉成了一條線,原本炯炯有神的雙眼,此時變成了收獲與滿足的相連。
午間的太陽有些烈了,父親從老農民變成了攔羊漢,他扛上攔羊鏟子,把羊群趕到山坡上吃草。微風中,這一個人一群羊,一座山頭一個秋天,把黃土地最后的收獲變成了黃草和落葉,悄然間勾勒出的塞上風光,盡顯黃土高原的稀疏。屋后那片高粱地,一眼望不到頭,母親站在高粱地頭,顯得矮小許多,那火紅的穗子似乎能浸染整個黃土高坡。只見母親左手抓住高粱穗子,右手用那并不鋒利的剪刀將穗子輕輕剪下,放進面前的紅柳筐里,不一會兒,高粱穗子便將紅柳筐填滿了,把裝滿高粱穗的紅柳筐提到不遠處的打谷場后,又開始剪新的一筐。繁雜的農村生活讓她的手長滿了老繭,與那夯土的石杵頗為相似。手雖然被剪刀磨出了水泡,但她似乎不知道疼,也不知道疲倦,就這么一人一剪刀,一片高粱地,不停剪裁著生活的希望。
落日余暉穿過那掛著零星葉子的白楊樹,晚風輕起,顧不得滿身疲憊的母親,給羊羔子加完草料后又開始張羅起了晚飯。父親扛著攔羊鏟子,背著似落未落的夕陽,趕著肚子鼓鼓的羊群進了羊圈。留在羊圈里的小羊羔,發出“咩咩”的叫聲,撒著歡兒尋找著自己的母親,與我小時候常纏在母親身邊的樣子很像。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已不能像從前一樣,圍在母親身邊,討要她藏在柜子里的零食。闊別家鄉多年的我,即便是春耕秋收,也難得回老家一趟,更別說是看父親趕著羊群回家,母親在地里忙碌的身影,以及在腦畔的山頂上等待夕陽的一抹余暉。
夜幕降臨,喜歡在院子里漫步的大公雞早早就鉆進了窩里,大黃狗也蜷縮在窩里,警覺地豎起耳朵。屋子里,父親小酌一杯散裝的烈酒,掬一筷子下酒菜,一臉滿足,母親掐著手指算著今天的收獲,仿佛糧食已經裝進了倉窖的架洞里。我靜靜地坐在一旁,看著他們臉上洋溢的幸福,感嘆這沒有城市的車水馬龍,沒有燈火輝煌的高樓大廈,卻有數不盡的收獲和滿足。不知何時,彎月悄然間掛在白楊樹的枝頭,夜空中的點點星光,安撫著孤零零的村莊進入了夢鄉,這一夜后,秋意便愈發濃郁了。
秋風瑟瑟搖杏樹,枯葉飛舞下枝頭。粟谷成黃透豐影,幾人曾見汗泉流。而今,又是秋意正濃時,在那個蝸居在黃土高原的小山村里,父親應該正在山坡上放羊,母親在撿畔底下的地里掰玉米,身后跟著幾只尋找蟲子的大公雞。(漢鋼公司 薛生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