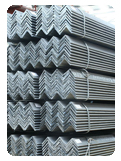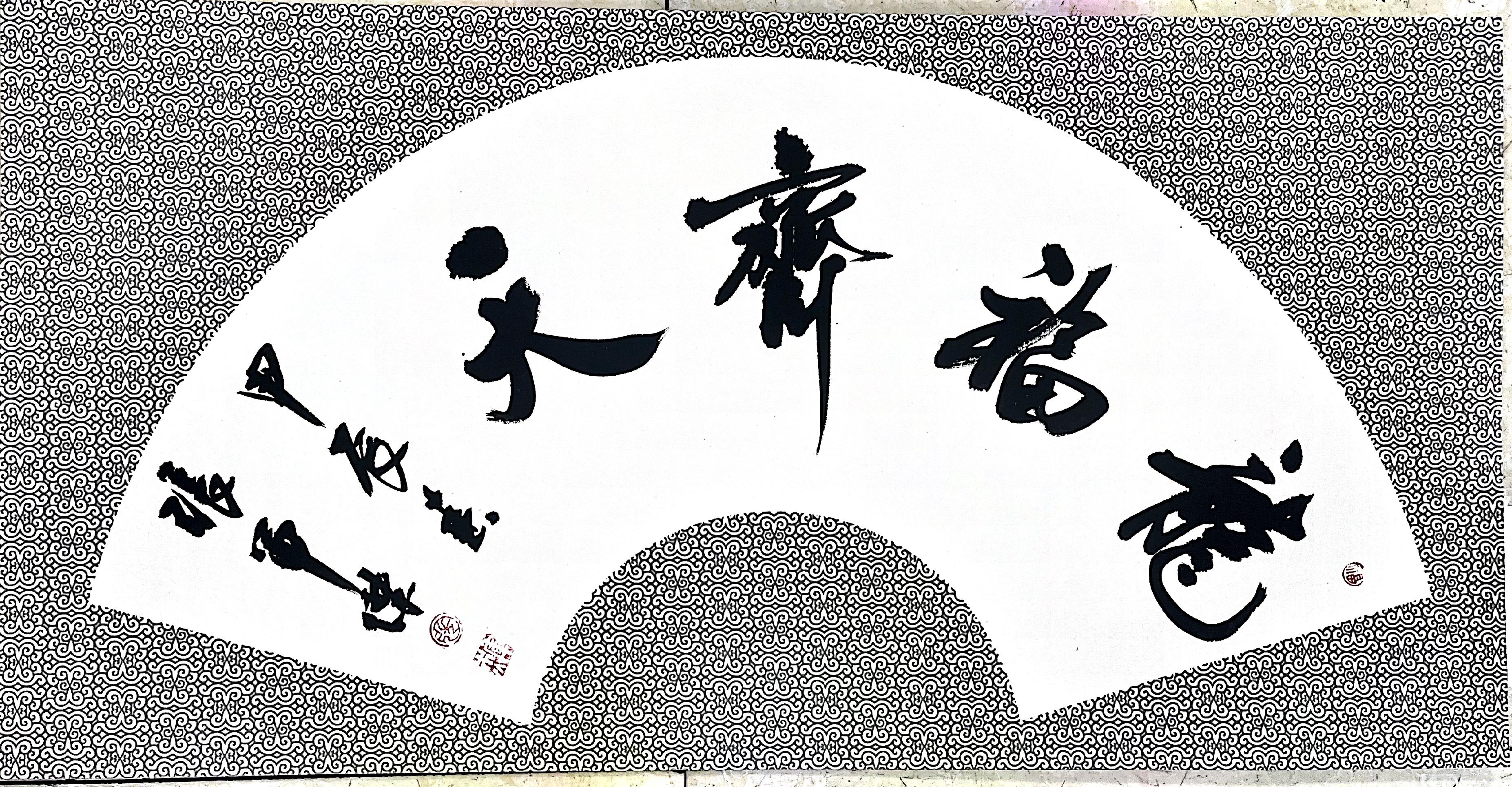“離離暑云散,裊裊涼風起。”當夏的余溫在暮色中褪盡,處暑便踏著細碎的秋聲而來。這凝結著時序智慧的節氣,既是溽熱的句讀,亦是清寒的序章,而覆地翻天的韻律里,鋼鐵的精神如潛流奔涌,與節氣的脈搏同頻共振,在寒暑交替間織就出一張無形的精神網絡。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釋“處暑”為“暑氣至此而止”,一個“止”字藏著時序輪回的玄機,恰如鋼鐵在熔煉與冷卻間找到的平衡節點。當驕陽收斂了灼人的鋒芒,長空愈發寥廓如洗,流云舒卷若素箋上的淡墨;大地經三伏炙烤后沉淀的靜穆,恰似百煉精鋼從熔爐中取出時的沉凝,那是在熾烈中淬煉的堅韌,是于嬗變中固守本真的篤定,鋼鐵的品格早已融進節氣的骨血里。
風過處,木葉簌簌作響,偶有幾片染了秋霜的葉瓣翩躚墜地,像誰不慎遺落的碎金。池沼里,殘荷褪盡鉛華,擎著半池靜水倒映天光云影,這份“留得枯荷聽雨聲”的倔強,正是鋼鐵在歲月里磨出的凜冽鋒芒。風雨侵蝕中始終向上的姿態,與鋼鐵在歲月里保持的挺拔一脈相承。宋人呂本中筆下“殘暑蟬催盡,新秋雁戴來”,道盡的不僅是時序之美,更是鋼鐵與自然共有的柔中蓄剛。
田疇間鋪展的金色錦緞,稻浪翻滾的弧度里藏著農人彎腰收割的剪影。他們黧黑的脊梁在秋陽下彎成堅韌的弧線,指縫漏下的谷粒裹著三季風霜,這份“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的堅守,與鋼鐵工人在軋機前千萬次的精準操作,本是同一種精神質地。單調中孕育的豐盈,重復里鍛造的奇跡,讓“處暑高粱遍地紅”的農諺,成為鋼鐵般意志在土地與車間共同刻下的年輪。
暮色漫過城市天際線時,廠區的高爐噴吐著橘紅火焰,與西天晚霞連成一片,仿佛將處暑的余暉鍛造成鋼。煉鋼工人防護面罩后,爐火映亮的眼眸里,藏著與農人同樣的專注。在鋼水奔流的眩光中校準參數,在軋機轟鳴里把握精度,這雙在高溫中穩健的手,既能托舉百噸鋼坯,也能捻起發絲級公差,恰如處暑時節的大地,經盛夏熔鑄仍葆有的蓬勃生機,在車間與田野間流轉。?
不妨在這樣的時節暫歇腳步,看晨露在草葉上凝成水晶,聽暮蟬唱盡最后的挽歌,或仰望銀河看流星曳尾。目光掠過工業區的高爐廠房,會發現鋼鐵鑄就的輪廓與遠山融為一體,超越冷硬的金屬質感,化作創新突破的勇氣。這正如處暑帶來的第一縷新涼,為時代生長注入的不竭動能,在自然與工業間無縫流淌。
處暑是夏與秋的渡口,一邊連著蟬鳴漸歇的喧囂,一邊通向雁陣驚寒的澄澈。陰陽消長的節點上,自然與人文的交響里,鋼鐵般的精神韻律始終回蕩。愿我們如處暑后的大地,在沉淀中積蓄力量;似百煉成鋼,于歲月里愈發顯露出溫潤而堅韌的光彩,讓節氣與鋼鐵的靈魂,在生命里和諧共鳴。(龍鋼公司 杜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