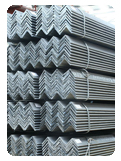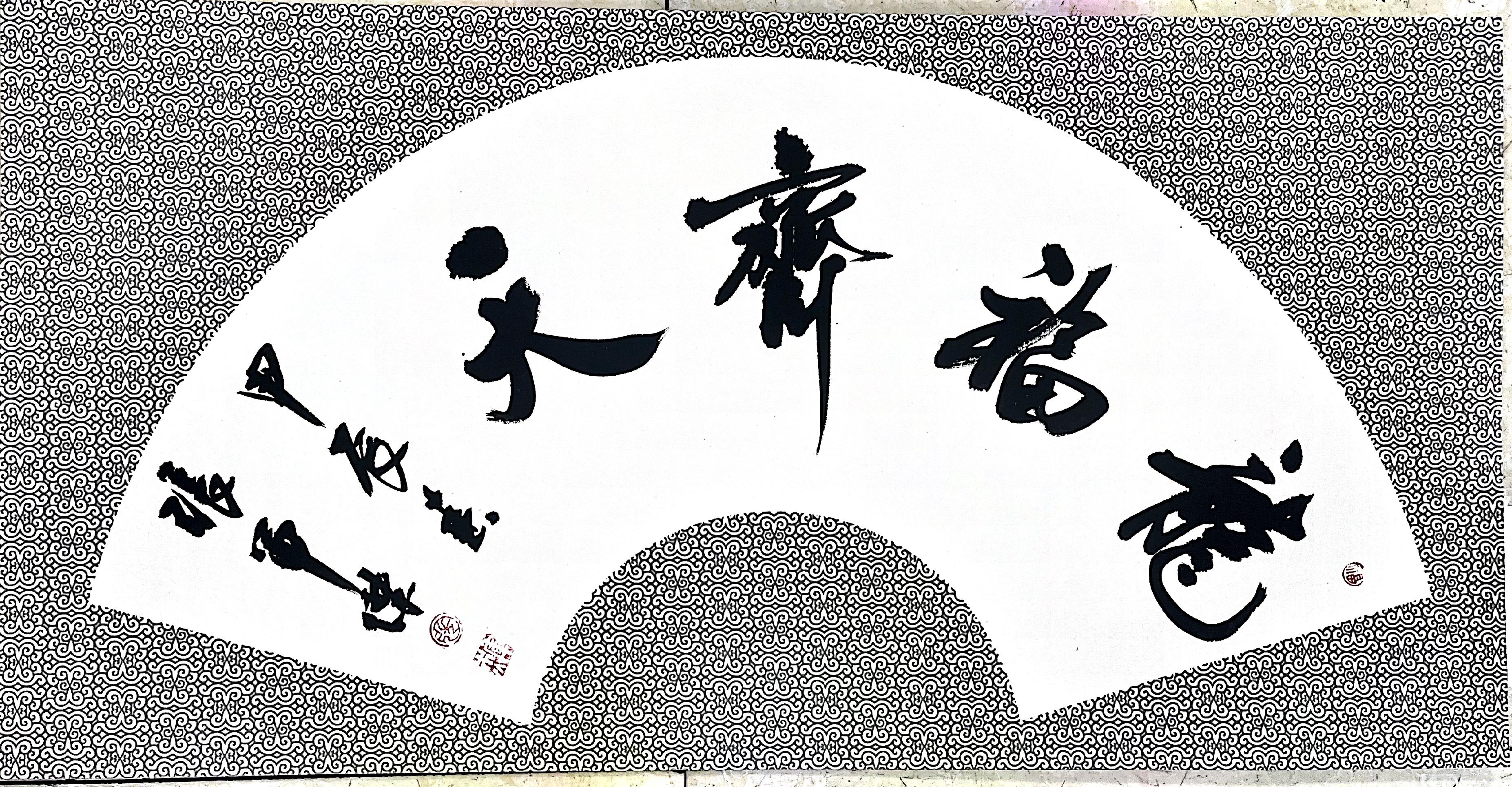秋的滋味,并非猝然而至的。它先是悄悄然潛入夜半的涼風,繼而沾染于清晨的草尖,最終才浩浩蕩蕩地席卷了天地,成為一種無可回避的、深沉而復雜的況味。
初秋是矜持的,像一位丹青妙手,提著蘸滿清水的筆,輕輕在夏日的濃綠上一點,那綠便悄然淡了,退了,于某些葉子的邊緣,泛出一絲若有若無的黃意來。天色也洗得高了,藍得透亮而空曠,云絮抽得極薄極淡,仿佛一聲嘆息便能吹散。此時的風,最有分寸,拂過皮膚,只帶來清透的涼,尚未夾帶蕭瑟之氣。早晚須得添一件單衣,這添衣的動作里,便已有了第一重秋的體味——一種小心翼翼的、生怕驚擾了什么的溫柔。
及至仲秋,這況味便濃郁起來,慷慨起來。它成了視覺的盛宴。楓樹、黃櫨,仿佛約好了一般,競相將積蓄了一生的色彩噴薄出來。那紅,不是單一的,有絳紅、猩紅、赭紅,層層疊疊,如燒如燎;那黃,也不是單調(diào)的,有金黃、鵝黃、橙黃,明明晃晃,似鎏似鍍。行走山野,如同步入一幅巨大的、正在肆意揮灑的油畫之中。然而在這極致的絢爛底下,卻藏著一種靜默的悲壯。因為深知盛極而衰的至理,每一片艷極的葉子,都是在用盡全部生命,進行最后的、告別式的舞蹈。此時的空氣里,彌漫著果實熟透的甜香,稻谷干燥的芬芳,還混雜著落葉腐爛時微醺的、屬于大地的氣息。這香味,豐厚而踏實,是秋天慷慨的饋贈,亦是它莊嚴的嘆息。
到了晚秋,況味便轉(zhuǎn)向深沉與蒼勁。繁華落盡,生命的骨架嶙峋地顯露出來。樹木刪繁就簡,只剩下疏朗的枝椏,鐵畫銀鉤般地分割著青空。原野卸下了濃妝,露出質(zhì)樸的、灰褐的胸膛,顯得格外遼闊而荒涼。秋風也變了脾氣,不再是“秋風拂面”,而是“秋風掃落葉”,帶著一股肅殺的、不容置疑的清理意味。它呼呼地刮過原野,卷起千枯的葉浪,發(fā)出干燥而脆響的聲音。此時的況味,是寒蟬的絕響,是蟋蟀在床下最后的低吟,是一種繁華過后、塵埃落定的清明與孤寂。人們縮著脖子走在風中,心頭或許會涌起一絲莫名的惆悵,為那逝去的溫熱與生機。
然而,秋的況味絕不止于衰颯。在那看似蕭條的表象之下,蘊藏著更為深厚的、屬于成熟的力量。你看那農(nóng)人古銅色的臉上,縱橫的皺紋里流淌著收獲的喜悅,那沉甸甸的谷粒入倉,便是對一年辛勞最踏實的注腳。秋,教會人們懂得收藏,懂得珍惜,懂得生命的豐饒來自于辛勤的耕耘,也懂得絢爛之極終歸于平淡的宇宙法則。
秋天的況味,是復雜的交響。它既有“采菊東籬下”的悠然,也有“萬里悲秋常作客”的蒼茫;既有“霜葉紅于二月花”的熾烈,也有“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凄清。它是一杯釀得恰到好處的酒,初品微涼,再飲甘醇,回味里卻帶著一絲苦澀與辛辣,教人清醒,也教人深沉。
它不似春之天真,夏之熱烈,冬之酷烈。它寬容、明澈、富于智慧。它讓我們在漸涼的天氣里,學會向內(nèi)尋求溫暖,在凋零的景象中,懂得欣賞風骨與留白。這便是秋的況味,須得年歲漸長,方能品咂出那千回百轉(zhuǎn)的層次,最終與之達成一種默契的、無言的和解。(漢鋼公司生產(chǎn)管控中心 郭超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