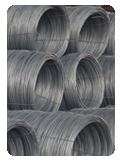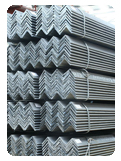周末母親念叨說老院子的雜物堆得快擋住門了,我便拎著布袋子一個(gè)人回到村里。推開門時(shí),午后的風(fēng)裹著墻根月季的香氣撲過來,客廳角落那口褪了色的木箱靜靜蹲在那兒,箱身落了層淺灰,像在等誰來翻撿藏在里面的時(shí)光。想起以前的“寶貝”都藏在這里,于是便蹲下身,打開箱蓋,時(shí)光嘩啦傾瀉,淌出半箱陽光,還有沉在箱底的“耐克”書包。
卡其色布料已經(jīng)泛白,像褪了色的大地,邊角磨出細(xì)密絨毛,針腳卻倔強(qiáng)隆起,繡出曲折弧線。那是母親照著雜志縫的“耐克”鉤,不像別的“耐克”一樣是黑色的,而是在小鉤里繡著小花、小草。
四年級(jí)的夏天,耐克書包風(fēng)靡全校。同桌把書包放在桌上,金屬拉鏈“咔嗒”一聲,吸引了半教室的目光。放學(xué)回家,便央求母親買書包,母親坐在縫紉機(jī)前,腳踏板嗒嗒響,“媽給你做新書包。”她頭都不抬地說道,“這鉤子很好縫的,不比買的差。”我盯著縫紉機(jī)上上下穿梭的針,想起同桌的黑色鉤子,臉上發(fā)燙。“不要!”我把舊書包摔在沙發(fā)上,拉鏈撞扶手,發(fā)出刺耳聲響,“同學(xué)都背正版的,這個(gè)一看就是假的,太丟人了!”
母親的手停在半空,縫紉機(jī)聲戛然而止。她拿起卡其色的粗布,對(duì)著光看布料紋理,輕聲說:“這料子結(jié)實(shí),洗多少回都不走樣。”后來她還是做了。趁我熟睡,臺(tái)燈亮到后半夜。清晨醒來,新書包放在床頭,卡其色的身子,側(cè)面縫著布兜,正面是歪斜的“耐克”鉤,針腳密得像怕它掙脫,小鉤底色是紅色的,上面總共繡了十個(gè)大小不一的小花、小草。
那天我沒背它,把它塞進(jìn)衣柜最底層,依舊背著舊書包去學(xué)校。放學(xué)回家,母親沒提書包,只是在我吃飯時(shí),說:“多吃點(diǎn),還要長(zhǎng)個(gè)呢!”
再見到它,已是十年后。指尖撫過書包,邊緣起了毛球,像老人下巴的胡茬,摸上去暖融融的。歪斜的“耐克鉤”依然如故,把書包翻過來,里襯是塊碎花布,該是母親年輕時(shí)的舊裙改的。布上繡著我的名字,針腳比鉤子整齊些,卻也歪歪扭扭,像初學(xué)寫字的孩童的筆跡。名字旁有個(gè)小補(bǔ)丁,用的是我幼兒園的床褥子,上面的小熊耳朵早已磨平。此刻看著補(bǔ)丁,眼淚啪嗒掉在布上,洇開一小片深色。
提手處有道深深的勒痕,是六年級(jí)春游時(shí),我背著這個(gè)書包,半路丟在草地上,和朋友玩“一二三不許動(dòng)”捉人游戲時(shí)遺落的。下雨了母親找到我,書包已濕了大半。是她把書包護(hù)在懷里,用外套裹著找我,一見我還笑著說道:“書包沒濕透,里面的白面饃饃還能吃。”說著把傘和白面饃饃遞給我就又往回走,我看著她的背影在雨中顯得那么單薄。
原來我早就背過它了。在我遺忘的時(shí)光里,它被母親的體溫焐暖,替我擋過雨,盛過饅頭,裝過我隨手塞的彈弓和秘密。
把書包輕輕擁在懷里,如同擁著整個(gè)童年。布料粗糙,卻比任何真皮的都溫軟;針腳歪斜,卻比任何機(jī)器縫紉的都規(guī)整。那個(gè)歪扭的“耐克鉤”,哪里是模仿?那是母親用半宿燈光、磨破的指尖、接錯(cuò)的線頭,一針一線繡出的印章,刻著“母親牌”三字,獨(dú)一無二。小時(shí)候總以為,體面是書包上的鉤子;長(zhǎng)大后才懂得,真正的體面,是藏在針腳里的心意。那些年母親縫進(jìn)布里的,哪里是線?是她舍不得添新衣的節(jié)儉,是她徹夜不眠的辛勞,是她見我皺眉時(shí)咽下的失落,是她從未說出口的“愛你”。最好的“耐克”,從來不是書包上的標(biāo)記。是母親彎著腰,將愛意縫進(jìn)經(jīng)緯的姿態(tài);是那個(gè)卡其色書包,在歲月里磨出毛邊,卻依然能盛下整個(gè)世界的溫柔。
在回城里的路上,我挎著充滿兒時(shí)回憶的書包,心中凝結(jié)出對(duì)母親的千言萬語,以及一句遲來的“我愛你”。(龍鋼公司 陳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