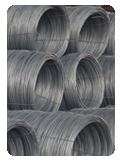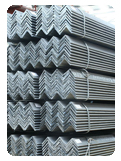晨霧未散時,教學(xué)樓走廊已響起細(xì)碎的腳步聲,是您抱著一摞作業(yè)本匆匆而過,發(fā)梢沾著秋露,衣角被風(fēng)掀起又按下。暮色四合后,辦公室的燈仍亮著,教案上的紅筆批注像星子,在紙頁間明明滅滅。這方三尺講臺,原本是最平凡的人間劇場,卻因您的堅守,成了最動人的詩行。
若說教育是一場溫柔的喚醒,教師便是執(zhí)燈的人。春日里,您俯身為趴在課桌上的學(xué)生理平皺巴巴的衣領(lǐng),指尖輕點錯題本上的紅叉,“這題像春天的筍,得慢慢來,急不得”;秋陽里,您站在講臺上展開中國地圖,用粉筆勾出黃河的蜿蜒:“看,這是我們的母親河,每一道彎里都沉淀著五千年的故事。”粉筆灰落進(jìn)您的衣領(lǐng),染白雙鬢,可您的眼睛始終亮著,那是春蠶食葉時的專注,是落紅護(hù)根時的溫柔,是嫩芽破土?xí)r對生長的渴望。
校園的梧桐葉黃了又綠,您的身影始終在時光里清晰如昨。早讀課的教室,您捧著保溫杯巡查,發(fā)現(xiàn)打盹的孩子便輕輕敲敲課桌;運動會的看臺上,您舉著相機(jī)捕捉?jīng)_刺的瞬間,卻在沖線處第一個迎上去扶住摔倒的學(xué)生;放學(xué)后的辦公室,您給成績落后的同學(xué)補(bǔ)完課,又從包里掏出面包,給晚歸的孩子當(dāng)夜宵。您常說:“教育不是灌輸,是點燃。”于是數(shù)學(xué)課上,您用月餅?zāi)>咧v圓的分割;語文課上,您帶學(xué)生去操場上觀察落葉寫作文;連最枯燥的歷史年表,都被您編成了押韻的歌謠。那些被您點亮的夜晚,那些因您而亮的星光,終將在某個清晨,長成孩子生命里的森林。
有人說教師是“燃燈者”,可您更像春溪,不疾不徐,卻能穿透頑石;像春風(fēng),無形無狀,卻能喚醒萬物。這些年,我們見過太多這樣的“春溪”:“扁擔(dān)校長”張玉滾以一根扁擔(dān)挑起深山里的課本,用二十一年的青春,守護(hù)著河南省伏牛山深處一所小學(xué)的光;“燃燈校長”張桂梅節(jié)衣縮食,每天的生活費不超過3元,省下的每一分錢都用在學(xué)生身上;還有“最美教師”張麗莉,在失控的客車前推開學(xué)生,自己的雙腿卻永遠(yuǎn)留在了那個夏天。他們用最樸素的方式詮釋著:所謂師者,不過是把“別人家的孩子”當(dāng)成自己的孩子,把“一時的事”做成“一生的事”。
我曾在青春里與這樣的光相遇。初二的我是辦公室的“常客”,不是因為優(yōu)秀,而是總把作業(yè)本落在操場、把試卷藏在書包夾層。您卻從未皺過眉,只是在我又一次“忘記”交作業(yè)時,拉著我坐在走廊的臺階上:“你看這棵梧桐樹,春天抽芽時也會掉葉子,可它從不停止生長。”那天傍晚,您陪我把漏寫的作業(yè)補(bǔ)完,夕陽把兩個影子拉得很長,您的影子里有我,我的影子里有光。后來我才明白,您不是沒看見我的頑劣,只是選擇相信,每顆種子都有自己的春天,有的早,有的晚,但一定會發(fā)芽。
蔡元培先生說:“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yǎng)和諧而穩(wěn)定的因素。”而教師,正是這和諧因素最直接的傳遞者。您用一支粉筆寫就的,不僅是公式定理、詩詞歌賦,更是做人的品格、處世的溫度;您在三尺講臺上耕耘的,不僅是四十分鐘的課堂,更是一個民族的未來、文明的火種。那些被您托舉過的孩子,終會帶著您的期待走向四方,有的成為醫(yī)生,有的成為工程師,有的回到鄉(xiāng)村當(dāng)老師。他們或許不會時常提起您的名字,但每當(dāng)他們蹲下來安慰哭泣的孩子,每當(dāng)他們認(rèn)真批改一份作業(yè),每當(dāng)他們在困境中選擇堅守,那束光就會從他們身上散發(fā)出來,像極了當(dāng)年您站在講臺上的模樣。
此刻,窗外的秋風(fēng)又起了。我忽然想起電影《一生只為一事來》里那句話:“我們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有希望。”原來這就是師者的信仰,用一生的堅持,去點燃無數(shù)個希望;用平凡的身軀,去托舉最遼闊的遠(yuǎn)方。
您是我青春里的燈,歲月里的詩,是所有關(guān)于美好的注腳。愿這人間永遠(yuǎn)有您這樣的人,愿這燈火永遠(yuǎn)明亮、永遠(yuǎn)溫暖。(龍鋼公司 王曄)